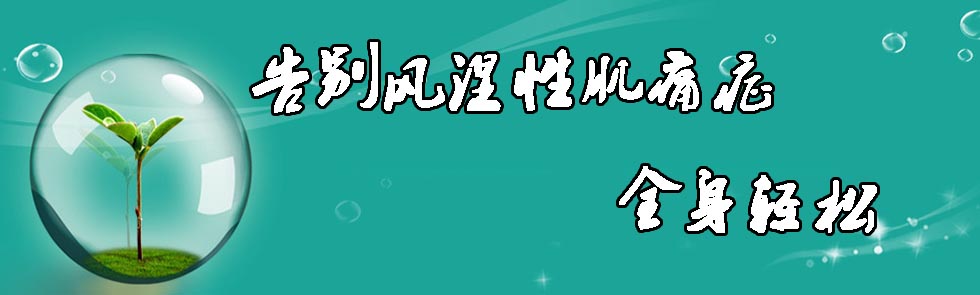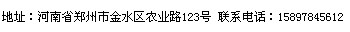在这三段发生在复医院的真实故事里,有许许多多已为人母和正在为此而努力的人的身影。
病治好了,她却不敢怀孕了琳达(化名)为了早日当上妈妈,在王凌医生那儿看病已经有大半年了。
可当王凌告诉琳达,病情已经好转,可以准备怀孕时,琳达却陷入了深深的纠结。
王凌不明白,40多岁的琳达还在等什么?
其实,怀孕的喜悦曾一次次降临到琳达的家。32岁那年,琳达新婚后不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,可几周后胎心停止,喜悦转眼变成了流产的痛。
琳达觉得,肯定是因为没做好准备,才会流产。休息了一段时间,她再次怀孕,结果竟和第一次一样,她再一次流产了。医生告诉琳达,她的子宫环境很不好、内分泌也有问题,即使再怀孕,也很难保胎。
琳达和丈夫都是知青子女,两人十分渴望一个温暖的家,而孩子是他们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35岁那年,琳达尝试了试管婴儿辅助生育,胚胎成功地移植到她体内,可相关的指标却一直很低,医院躺了足足60天,西药、中药都吃遍,最终还是流产了。
几年来,先后经历六次流产的琳达几乎医院,由于时不时请假保胎,工作早已无法继续。
有一次琳达去看医生,排队时和边上的病友聊起了自己的经历,一旁病友的丈夫低声嘀咕了一句:“如果在我们老家遇到你这种情况,丈夫早就要离婚了。”
琳达的丈夫听不下去了,他蹭一下站起来,激动地和眼前这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争论起来。
回到家,夫妻二人长谈了一次,丈夫对琳达说,不能这样无限期地折磨自己,“如果到了40岁还没有孩子,我们就不生了。”琳达答应了。
几年来不停地看病,琳达结识了不少和她有类似经历的病友,只要听说有年龄和她差不多的,甚至情况更复杂的病友怀孕,她都感觉自己还有希望。尽管多次的流产已经让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脆弱,尤其是子宫腺肌症已经导致她的子宫比常人大了许多。但值得庆幸的是,医生告诉她,她的卵子储备还不错,只要还有卵子,就有怀孕的希望。她心里也始终相信,自己一定会有一个孩子。
40岁那年,琳达又怀孕了,这医院,还吃一种过去从未尝试过的食疗方,可这种药让她全身水肿,肿到连话也说不出。
最终,孩子还是没能保住。丈夫郑重地对琳达说:“放弃吧,不想再看你这样受苦了,没有孩子,我们还是可以过得很好。”琳达流着泪,同意了。
几天后的一个下午,琳达在病房里无意中听见护工说,有人在楼梯口哭。她起身,慢慢地挪步到楼梯口,却惊讶地发现,流泪的那个人是自己的丈夫。
丈夫一边劝她放弃,一边却背着自己悄悄流泪,琳达觉得这比失去孩子更让她痛苦。那一刻,她决定,无论如何都要生一个孩子,为了自己,更为了丈夫。
由于流产后恶露总是不断,琳达去了复医院,医院的琳达在选择医生时变得谨小慎微,她连续去了王凌的门诊好几次,都不急着看病,而是在一旁观察,直到她认定王凌是个既亲切又负责的医生,才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。
在解决了恶露的问题后,王凌建议琳达进行封闭抗体治疗,通俗地说就是将她丈夫的血液抽出一定的量打入琳达的体内。
封闭抗体针必须打在手臂内侧,但此处的皮肤很薄,打针时非常痛。琳达告诉王凌,再疼她也要打。
可随后的检查发现,琳达丈夫的乙肝指标呈阳性,治疗计划只得搁置。无奈之下,一家人反复商量,最终决定用琳达丈夫弟弟的血液来替代。
熬过了半年的封闭抗体治疗,再加上其他一系列内分泌治疗,琳达终于等来了可以怀孕的消息,可本该高兴的琳达却犹豫了。她流着泪告诉王凌,她不是不想,而是不敢再怀孕了,自己常常都会做恶梦,而梦中的情节几乎无一例外,都是流产。
作为妇产科医生,王凌太清楚为了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,那些想当“妈妈”的女性付出了多少努力,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。王凌试着安慰琳达,但她知道,作为医生她已经做了她能做的,心里的这道槛只有靠琳达自己过。
有很长一段时间,琳达都没有再来看过病。几年后,王凌收到了琳达的消息,她有了一个健康的儿子。
怀上了,终于可以回老家了在医院付费处的角落里,小郑(化名)和丈夫仔细数着手里的钱。这几百元钱他们已经数了好几遍,这是他们身上的最后一点钱,可是离治疗费还差很多。
小郑和丈夫是同乡,十年前,两人刚结婚那会儿在老家的小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店,原本美满的小日子,因为小郑的不幸流产而突然中止了。
自从那次流产后,小郑的肚子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动静。迫于婆家的压力,医院检查,医生说她的输卵管不太通畅,想生孩子很困难。
得知了检查结果,小郑的公婆立即对儿子表态:既然媳妇儿生不出孩子,就离婚吧。
“我绝对不会跟她离婚的”,小郑的丈夫很坚决,他决定把房子买了,到大城市给小郑治病。
从安徽到浙江,夫妻医院好,医院,都会去试一试,医院,一个小手术动辄就要花去几千元,小郑的丈夫也丝毫没有犹豫。他一心认为只要能让小郑好起来,花多少钱都值得。
一眨眼四五年过去了,小郑和丈夫花去了卖房得来的所有积蓄,可小郑依然没有怀孕。两人决定,去上海再看一看。
夫妻俩来到复医院,中西医结合科许钧医生的话让小郑吓了一跳:“你的卵巢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,如果想要孩子,赶紧做试管婴儿吧,再拖下去,连试管技术可能也帮不了你们了。”
可是,两人拿出了身上所有的钱,根本凑不齐试管婴儿的治疗费用。
为了攒下足够的钱,他们决定留在上海打工。小郑找到了在厨房帮工的活儿,丈夫则在工地上做建筑工。
每隔几个月,只要攒下一点点钱,他们就会去找许钧看病,而许钧则会想办法为他们用最节省的方法治疗。
一年后,许钧建议小郑再做个输卵管造影看看,但小郑却表示,还是不做了吧,省点钱,能不能怀上就看老天爷了。许钧告诉她,只要心态放松了,有些多次做试管不成功的夫妻也能自然怀上。
又过了一阵,小郑高兴地告诉许钧,自己怀孕了,等过了三个月,他们就准备离开上海,因为这里的生活费对他们而言实在太贵。
“那你们打算去哪里?”许钧问。
“回老家啊,怀上了,终于可以回去了。”小郑说。
等孩子出生,给TA讲哥哥的故事徐喜娣今年45岁,她曾经是一位母亲。如果她的儿子还活着,今年应该22岁了。
医院里但凡认识徐喜娣的医生和护士,大都在她丈夫的手机中看过她儿子生前的照片。说起儿子,她的悲伤中透露着骄傲。
他们的儿子叫李本超,两年前的夏天,是他大学毕业前最后的一个暑假,已经找到工作的他回了一次安徽老家。
那天下午,李本超在好友家里玩,忽然听到村里有人喊:有人掉进水库里了,快去救人!李本超和好友急忙骑车赶到水库边,只见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在水库中挣扎,两人立即跳进了深达数米的水库。
两个孩子都被救上来了,李本超却没有上来。
儿子去世后,原来的家徐喜娣再也住不下去了,她无法待在留有儿子过往生活痕迹的房间里。
搬离了老家,思念和悲痛依然断不了。无心再工作的徐喜娣每天望着空荡荡的房间发呆。有时候在路上见到高高瘦瘦男孩的背影,她会忍不住上前去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儿子。
去年,徐喜娣夫妇做了一个决定:再生一个孩子。医院,医生都告诉她,她的卵巢功能已经衰退,无法再生育了,即使做试管婴儿也是浪费钱。
徐喜娣和丈夫商量,医院再看看,如果那里的专家也说没希望,他们就放弃。
考虑到丈夫的表亲在上海打工,徐喜娣决定去上海,在复医院里,他们仔细看了一遍专家栏里的介绍,最终选择了孙晓溪医生。
没想到,孙晓溪也做出了和之前的医生同样的判断,徐喜娣当场哭了。听说了夫妇二人失去儿子的事后,孙晓溪决定试一试。
在儿子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徐喜娣情绪低落,她的月经都没有来,后来就成了好几个月才来一次。
孙晓溪认为,治疗的第一步是先让她的月经正常起来。用药后,徐喜娣的生理期逐渐正常了。在检查时,医生惊喜地发现她体内产生了一个卵泡,这枚珍贵的卵子,意味着生命的希望。
为了获得更多的卵子,孙晓溪开始为徐喜娣进行促排卵治疗,几个月后,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为他们配成了5个胚胎。
正当徐喜娣以为可以迎接来之不易的胚胎时,她被查出了宫腔息肉,必须尽快手术才能进行胚胎移植。她又一次上了手术台,此前的两次取卵手术,她都坚持不打麻药,尽管医生告诉她,这么小剂量的麻药对卵子质量其实并没有影响。
今年春节,成功移植了胚胎的徐喜娣终于盼来了怀孕的消息。为了这个小生命,她和丈夫医院附近几十元一天的小招待所里,房间里除了床什么也没有;为了这个小生命,医院还想办法为她捐助了一部分治疗费用。
然而,再为人母的喜悦只维持了短短40多天,40多天后,胚胎停止了发育,徐喜娣再一次上了手术台。
前后经历了六次手术,徐喜娣的丈夫很为妻子感到心疼。他对妻子说,如果剩下的胚胎移植还不成功,我们就放弃吧。
徐喜娣却很坚持,她说,只要有希望就一定要试下去,她盼着孩子出生的那天,给TA讲哥哥的故事。
来源:上海观察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